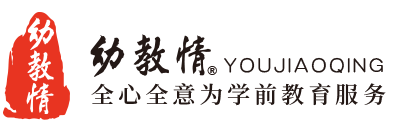刘晓东:“幼小衔接”应向“小幼衔接”翻转
来源:幼教情 日期:2021-03-09 阅读:0
2018年10月11日下午,由日本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两位教授陪同,我们一行访日人员参观了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小学。这所小学当时正值140周年校庆。副校长神户佳子女士向我们介绍了附小的概况和办学理念。印象最深的是,这所学校以儿童为中心展开一切课程。“儿童中心”这种观念已经在中国被批倒批臭,目前依然难以立足。但在日本这所著名的小学,他们的课程哲学始终是“儿童中心”。
副校长神户佳子谈到了“小幼衔接”问题。中国有“幼小衔接”,没有“小幼衔接”。但她谈的是“小幼衔接”。两种不同的称谓,体现了中日不同的教育观念,不同的办学思想。
长期以来,我对“幼小衔接”问题有许多困惑乃至抵触情绪。我反对“幼小衔接”背后的理念。我以为,解决“幼小衔接”问题,其出路在于幼儿园和小学都应当对接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在理论上,如果双方都能对接儿童,就不存在幼儿园和小学相互衔接上的困难;在现实上,如果双方都愿意对接儿童,就不应当存在幼儿园衔接小学,而只应当存在小学衔接幼儿园。当了解到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小学“小幼衔接”的提法和做法时,便又一次激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从“幼小衔接”到“小幼衔接”:背后有大是大非
中国的“幼小衔接”主要是幼儿园的任务,小学只是“坐享其成”,以至于为了与小学对接,许多幼儿园大班的幼儿要专门上“幼小衔接”课。“幼小衔接”其实质是让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提前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纪律、教学等。而问题在于,小学的学习、生活、纪律、教学等所体现的“小学文化”本身,是值得反思的。
近年来,众多幼儿园由于儿童观、教育观的进步,已经意识到这种所谓“幼小衔接”与学前儿童的生活特点、成长需要以及学前教育的使命是相悖的,于是相继取消了“幼小衔接”课程。当幼儿园将“幼小衔接”作为自己的分内工作时,他们眼中盯着的不是幼儿,而是小学,并无条件地履行“幼小衔接”的所谓职责,不惜以牺牲幼儿的天性和生活为代价。而当幼儿园在理论视野里“发现”了幼儿,它们当然会拒绝继续进行违背幼儿的成长轨迹、成长规律、成长需要的所谓“幼小衔接”。
但中国的小学招生工作是指挥棒,大班幼儿确实存在幼儿园教育标准与小学教育标准的衔接问题。既然有的幼儿园已经断然取消“幼小衔接”课,但并不能消除幼儿园和小学之间实际存在的断裂现象。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收费的“幼小衔接班”,专门按照小学尤其是小学名校的“高要求”,来满足大班幼儿家长的急切需要。
但在日本不存在这种情况。日本是小学主动衔接幼儿园,所以称为“小幼衔接”。“小幼衔接”强调小学与幼儿园有“适当差距”,强调幼儿入小学应当“平缓过渡”而非急拐弯。我所见到的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小学1—3年级教室的环境设计、桌椅摆放乃至学习方式,都很像当前中国的幼儿园。我还看到,二年级学生那天依然在扎堆玩积木。可见,日本的小学存在“幼儿园化”现象。相比而言,我国不只是幼儿园存在“小学化”问题,我国的小学更存在严重的“小学化”问题;不只是小学自身存在过于“小学化”问题,它的“招新”试题的难度倒逼幼儿园变成“小小学”,即倒逼幼儿教育“小学化”。是到了应当反思中国当前的小学教育学、小学教育制度、小学教育文化的时候了!
日本的小学主动衔接幼儿园,尽可能向幼年方向做衔接,而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尽可能向高年级做衔接。其间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的高下优劣立见其间。
这涉及一个民族对其年幼一代,是急切地使其进入成人世界,还是成人世界顾惜童年,尽可能让年幼一代充分占有与其年龄相应的天性资源,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扎稳打”,走实走好成长的每一步,从容享受童年时光,乃至整个社会(尤其是成人社会)尽可能拥有童年的大问题[1]。这是大问题,是大学问,是大是大非,不可不察。
我想强调的是,儿童身上的天性资源是人世间最为宝贵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对与儿童年龄相应的天性资源不予充分珍爱顾惜,这是最大的暴殄天物。
二、“幼小衔接”背后的中国小学教育“综合征”
“幼小衔接”与“小幼衔接”不只是词序的简单倒置,而是体现了两种教育的不同性质。“幼小衔接”是以儿童以外的小学文化(小学教育的目标、任务、教材、学法、教法等)为标准,要求学前儿童一旦成为学龄儿童迈入小学,就要立即适应这种小学文化。为了适应这种小学文化,长期以来“幼小衔接”成为幼儿园大班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前教育在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以致近年来存在学前教育界普遍抵制“幼小衔接”的情况,并且已体现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也就是说,人们意识到“幼小衔接”是背离学前教育的目的与任务的。但在这一点上,小学教育界显然落后于学前教育界。一些名校在小学招收新生时的“考题”暴露了小学门槛的“高大上”,但这种“高大上”恰恰暴露了小学教育界的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已然落后落伍。仅就“幼小衔接”来说,他们眼中有的是“考题”,但没有对童年的了解,没有对童心的呵护,没有担当起关爱儿童的责任。说穿了就是,不懂儿童,不懂儿童与教育的关系,不懂小学教育的使命,背离小学教育的使命。既然存在如此若干“不懂”,幼儿园的幼儿一旦成为小学生,他们在小学的教育生活是怎样的,也就可想而知了。近几年教育部不断要求小学为小学生“减负”即可见一斑。官方的要求是一回事,小学是否有效为小学生“减负”是另一回事。小学教育继续将学业与成长对立起来,理直气壮地认为学习必然就有负担,必然就有压力、不愉快乃至痛苦。有这种教育学理论存在,小学生是不可能从学业负担中获得解放的。是到了应当反思中国当前的小学教育学、小学教育制度、小学教育文化的时候了!
小学教育界依然只以“小学文化”为本,而非以“儿童文化”为本。这里的以小学文化为本,其实质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小学教育观,是一种缺失现代儿童观的小学教育观。这就造成当今中国的幼儿园与小学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可笑又可恨的是,这种断裂是由社会上的“幼小衔接班”来造桥连接的。学前教育做得好的地方,几乎所有大班儿童必须要通过此“桥”才能“顺利”适应小学文化。据说,在某些城市,午饭过后,幼儿园大班便人走楼空。去哪里了?去坊间私人开设的“幼小衔接班”提前学习小学课程了,否则难以应对小学“招新考试”而进入小学名校。这是小学教育之耻!这是小学名校之耻!是到了应当反思中国当前的小学教育学、小学教育制度、小学教育文化的时候了!
小学,尤其是小学名校,面对入学儿童,不是以儿童的年龄特征为标准,而是在儿童以外另立“教育标准”。这种标准不惜让儿童抛弃他的年龄特征。这不是对童年的尊重与爱护,而是对童年的践踏与破坏。
当前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幼小衔接”问题,还有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等一揽子“综合征”。针对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基础教育已发起数次改革,但学业负担未见减轻,反而愈来愈重。问题何在?学业负担重与“幼小衔接”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儿童,没有让儿童在教育学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
小学教育改革、基础教育改革如果不能跟从儿童,不以儿童观的现代变革为引导,那么,这种改革就会以确保基础教育扎实,而不是确保教育应当扎实地落实在儿童的内在发展上。于是,这种改革就难以真正落实到尊重儿童、爱护儿童、解放儿童上,就总是以确保基础教育扎实的“伟大优点”、“伟大使命”为理由来压迫儿童、毁坏童年。例如,教育专家会理直气壮地说,学习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可能总是愉快的,等等。这些老调之所以能够一再重弹,正是因为不愿意承认儿童在教育学中的核心地位,不愿意承认儿童及其健康成长是教育的首要目的,就会堂而皇之地以牺牲童年的幸福与成长为代价来推动知识、道德、技能等方面的学习。学业负担过重其背后的教育学弊病就隐藏在这里。
“基础教育扎实”,“教育应当扎实地落实在儿童的内在发展上”,都没错。试问,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显然,我们当前的选择是“确保基础教育扎实”。但是,如果“基础教育扎实”沾满了让儿童没日没夜做各种作业的疲惫乃至血泪(即便儿童多获得了一点点知识、技能、“道德”,甚至在某些著名的国际性教育测评中屡屡取胜), 那么,这种蜚声世界的“基础教育扎实”还名副其实吗?以牺牲“儿童的内在发展”为代价的“基础教育扎实”是虚假伪劣的。如果“基础教育扎实”是以牺牲“儿童的内在发展”为代价的,那么,这种教育便是反儿童的,是不人道的,是反文明的,是野蛮的。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小学教育便存在与此相关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到了应当反思中国当前的小学教育学、小学教育制度、小学教育文化的时候了!
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不能只靠学前教育界来解决。小学教育界应当高度重视小学与幼儿园的衔接问题,将与幼儿园的衔接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应积极主动地去衔接幼儿园,而不是推给学前教育界。这是考验小学教育界是否具有儿童本位的教育观的重要尺度之一。
小学与幼儿园的衔接问题,表面上看是两种教育机构的衔接,但其实质是教育机构与儿童的发展、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的衔接。当前我国出现的“幼小衔接”问题表明,小学教育对儿童的成长需要、成长轨迹、成长规律是懵懂的、麻木的、迟钝的。
在这方面,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小学的做法值得借鉴。
三、为什么中国依然是“幼小衔接”而不是“小幼衔接”
极“左”政治时期,教育学界批判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的“儿童中心论”,批判斯霞的“母爱教育”,儿童文学界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尽管改革开放后对这些“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是,“儿童中心论”等观念已被批倒批臭,对“儿童中心论”的敌意已经附着在某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已经躲藏在某种文化无意识心理的深处,因而儿童在教育学中的核心地位一直未被承认,儿童本位的教育学(或发生学的教育学)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这就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在幼儿园和小学的衔接问题上,长期以来,不只是小学认为这是幼儿园的任务,幼儿园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的分内事。无论是1950年代从苏联传入的学前教育学教材,还是后来国内自编的学前教育学教材,往往都将“幼小衔接”作为独立的一章内容。也就是说,起初,“幼小衔接”这一提法和做法不能全都推给小学教育界。但改革开放后,经过皮亚杰发生论的儿童心理学的传播、童年研究的推进以及意大利瑞吉欧方案教学的洗礼等等,中国的学前教育逐渐构成以儿童为本位的新范式。但是,当学前教育界发生这些范式变化时,小学教育并未产生相应的范式变化。
这表明中国的小学教育与学前教育存在断裂问题。尽管“大教育学界”(学前教育学界往往将学前教育学以外的教育学术圈称为“大教育学”或“大教育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如成尚荣[2]等)倡导“儿童立场”或类似观念,但在大教育学界依然未能形成将儿童作为教育起点的氛围和声势,许多人对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是抗拒的甚至是反感的。一旦有人强调儿童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他们不是支持,而是斥之以“不专业”。说到“专业”,这涉及教育学的历史与逻辑。现代教育学恰恰是从“发现儿童”为开端的。如果将主张儿童在教育中处于中心地位斥为不专业,那么,这些批评者真应当补补现代教育学史、现代教育学原理等专业必修课了!
呼吁儿童立场的成尚荣等人主要属于中小学行政与实务管理层面,他们的教育学研究不属于学院派,或者不被认为是学院派,也不被“真正的”学院派认同、接受。成尚荣与笔者交流时便有这种“自嘲”。我以为,成尚荣做过小学教师,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的经历经验,他和一大帮与他有类似工作背景的人之所以主张儿童立场,之所以能提出儿童立场,是有经验支持的,是有切肤之痛的,是有教育反思的,因而是值得关注、值得信赖的。值得一提的是,“儿童立场”其实是“儿童中心”或“儿童本位”的另名。
在当前的中国,大学里许多专家往往会拒绝接受“儿童立场”(或“儿童本位”)这种理念,他们反对儿童在教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支“反动”力量。
当然,学院派的教育学者已经有人意识到儿童研究、儿童本位对于现代教育学建设以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例如,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倡导,于2017年9月在南京召开了“儿童成长与教育变革”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以“儿童”作为教育学的关键词,在20世纪下半叶“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段历史时期是很难的;改革开放后40年来,以“儿童”作为教育基础理论会议的关键词,这也可能是第一次。儿童在教育学体系中获得关键地位,尽管依然不是核心地位,但有走向中心的趋势,实际上是向中心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中国的教育学来说,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
四、“幼小衔接”向“小幼衔接”翻转的理论问题
儿童走向中心,这是卢梭教育思想的精髓。从卢梭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杜威、蒙台梭利,直至意大利瑞吉欧教育的领导者马拉古奇,均是如此。按照杜威的说法,卢梭的教育概念是“教育即自然发展”[3], 杜威自己声言“教育即生长”,并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对“教育即生长”这一命题有了不起的贡献。明眼人一眼就能认出,“教育即生长”其实质依然是卢梭的“教育即自然发展”。卢梭教育思想的核心即他的“自然教育”概念。他是如何界定自然教育的呢?“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4]“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其实就是儿童的身心的内在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皮亚杰发生学的儿童心理学便是(主要从认知层面)研究儿童的内在发展的。
卢梭认为,“人的教育”必须以“自然的教育”为前提,必须与“自然的教育”相一致。“遵循自然,跟着它给你画出的道路前进。”“这是自然的法则。你为什么要违反它呢?”[4]这就是说,教育必须以儿童为本位,教育学必须是发生学的。
许多人会说,这是西方的,不是本土的,因而必然会水土不服,我们应当另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教育学。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强调儿童本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一点儿都不比西方差。从老子、孟子,到宋明心学乃至理学,尤其是到了王阳明那里,再进一步到作为阳明左派的泰州学派,直到明朝晚期的罗汝芳、李贽那里,中国有一套童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强调童心(赤子之心)是文化的源头,强调成人应当通过复归婴儿、不失赤子之心来达成个体人生的圆满修炼[5]。如此看来,西方现代儿童教育学的儿童中心论与中国传统的童心主义不是可以相互会通相互支援的吗?
教育学的最大问题——当然也是教育改革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我们许多人既反对西方的“自然教育”学,又抛弃中国固有的童心主义传统,以至于文化主义、教育主义——其实就是与古代中国人“道法自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相背离的人为主义——汹涌泛滥于教育学界,致使教材、作业、考分等等将童年所吞噬或湮没。以至于一位文艺学学者由此悲愤而激越地说:“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儿童为敌’的文化环境里。……在那里,儿童的形象可以被随意涂抹,儿童的情感可以随意被蹂躏,儿童的意志可以随意被强奸。”[6]这是文化批评,也是教育批评。或许这一批评太过直接,或许十分激进。被批评的文化、被批评的教育肯定会倍感冤枉:“我们是关爱儿童的,我们是为了儿童好。”确实如此。但在某种分寸上,这种批评不也是一种白描、不也有它的理由吗?当那么多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在学校忙碌一天之后,还要将老师布置的作业带回家忙到很晚,学校对此如何解释?社会对此如何解释?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不是毁坏童年?当前的文化和教育真可谓与中国古代的童心主义云泥相隔、判若天壤。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是时候了,为古代中国人的童心主义思想招魂!是时候了,“救救孩子”!!
五、努力实现幼教界和小学界的衔接、学前教育学界与“大教育学界”的衔接
真正实现从“幼小衔接”到“小幼衔接”的转向,需要旗帜鲜明地树立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念,努力实现另两个“衔接”:幼教界(往往又被称为“学前教育界”)和小学界的衔接、学前教育学界与“大教育学界”的衔接。
“幼小衔接”到“小幼衔接”的转向,并非简单地从幼儿园衔接小学转变到小学衔接幼儿园。表面上看,“小幼衔接”是小学与幼儿园衔接,但实质上,是小学主动与幼儿园文化直接衔接,主动与从幼儿园大班而来的儿童直接衔接。如果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都以儿童为准,都向儿童看齐,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问题。
在这一点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小学乃至“大教育学界”稍稍回头,对学前儿童和学前教育有所了解;不只看社会与教育对儿童的需要,更要看儿童对社会与教育的需要;要有追根溯源意识,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完整的“儿童”概念,进而形成完整的“教育”概念。也就是说,所有教育工作者(包括学前教育界,但不限于学前教育界,还应当包括大教育学界)均面临儿童本位意识的建设问题。
实现学前教育学界与“大教育学界”的衔接,是教育学界的当务之急。但这两“界”的衔接是有困难的。何以见得?大教育学界往往认为学前教育是“小儿科”,学前教育学界理论水平低。这导致大教育学界不愿意与学前教育以及学前教育学界发生深层接触,但我以为,这恰恰也是大教育学界应当主动对接学前教育学界的理由。
何以见得?作为在编的学前教育学学科的一员,我与不少学前教育学界的学者一样认为,无论从学科视野、理论思维、理论深度、理论成果等方面,学前教育学界与大教育学界相比是处于弱势的,因此,学前教育学界必须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走进大教育学界,向大教育学界学习、取经,不断开拓学前教育学界的视野。更何况,学前教育学界和“大教育学界”同属于教育学界,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所以,学前教育学界没有理由不与大教育学界对接。
同样,大教育学界也没有理由不与学前教育学界对接。正如我与学前教育学界的一些学者所认同的,正因为学前教育学界理论水平低,学前教育学界就特别需要大教育学界关注学前教育学界,主动探究学前教育学界的主要学术问题,提高学前教育学界的学术水平。这是大教育学界应当与学前教育学界对接的理由之一。
“大教育学界”应当与学前教育学界对接,还有其他理由。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开端与起点,后来的教育其对象虽然不是学前儿童,但却曾是学前儿童。从了解教育对象——儿童——及其发展轨迹、成长规律和所受教育情况这个需要出发,大教育学界也应当了解学前儿童和学前教育,主动与学前教育界对接。这是大教育学界应当与学前教育学界对接的理由之二。
大教育学界应当与学前教育学界对接,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学前儿童、学前教育是将大年龄的儿童和大年龄的儿童教育的种种关系有所放大,所以说,学前教育学在教育学科群中具有独特的、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在世纪交接之际,我曾谈过这个问题:“由于学前儿童的主体发育水平与成人有很大差距,在学前教育那里,教育对象与学校教育中的教育对象相比,其种种特征都得到了放大,这种放大实际上是对普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种种特征的放大。所以,研究学前教育学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普通教育学。”[7]
杨适在其《哲学的童年》中写道:“那最初的思想本身却有原始的丰富性,往往在单纯中蕴含着后来发展的各种萌芽和因素,有它的特别的机制和有机结构。粗心大意的人不注意这一特点,对最初的东西以为一看就知道了,不过如此而已,便一掠而过。然而我们看到真正的科学家却从不轻易放过它们,他们总是对开端的东西不厌其烦地翻来覆去地加以研究。”[8]这是说开端的重要性。古代中国人就特别重视开端的丰富意蕴。例如老子提出“复归婴儿”,孟子认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先秦《学记》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专门文献,它是以这句话收尾的:“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三王祭祀百川的时候,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因为河是水的源头,海是水的归宿。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这是说,教育学应当尊重儿童发展的源头,应当尊重教育的开端,是谓“务本”。海德格尔所谓“从本有而来”的思想,也是告诉我们开端的重要性。而现代教育学的本质是发生学的教育学,是儿童本位的教育学。既然如此,处于儿童成长开端的学前儿童,处于教育体系开端处的学前教育,在教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便昭然若揭。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礼记·大学》)不去了解学前儿童、学前教育,那么,你就没有跨越教育学的那道必经门槛;不跨越学前儿童、学前教育的这道门槛,那么,你怎么能在教育学学科登堂入室?一旦跨越学前儿童、学前教育的这道门槛,你也可能突然发现,你原有的教育学由于缺少对“学前儿童”和“学前教育”的把握和发现,竟然有重大缺失。如果你的教育学不是以儿童为开端,那这种教育学还是现代教育学吗?而学前教育学往往会促使你去发现儿童,认识到教育学的起点应当是儿童。所以,任何将教育学研究作为志业的人都应当去“学前儿童”和“学前教育”那里开疆拓土。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如果说教育学是21世纪的中心学科的话,那么目前被视为‘小儿科’的学前教育学将会成为教育学科群中的一门显学,将会成为教育学科群中受人关注、受人器重的少数几个中心学科之一。”[7]
不只是大教育界要高度认识到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的重要地位,学前教育界也应当认识到学前教育、学前教育学的重要地位,而不应妄自菲薄。
如果大教育界能主动对接学前教育界,主动介入甚至占领学前教育基础问题,那么在当下中国,不仅可能对教育原理、教育哲学、课程论的视野有所拓展,境界有所提升,甚或能引起中国的教育学范式革命。为什么会引起范式革命?因为一旦介入学前教育,就必然关注到“儿童”这个研究对象。不了解儿童,在学前教育领域便几乎寸步难行,除非采取哄蒙骗的方式或暴力强制方式。一旦了解到儿童研究的重要性,一旦意识到儿童是教育、教育学的开端,那么整个教育学便会发生范式革命。现代教育学就是从“发现儿童”开始的。卢梭的《爱弥儿》便是榜样,这是历史的昭示[9]。正是欧美出现了“儿童研究运动”,才应运而生出杜威、蒙台梭利这些教育学大家。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种种史料显示,没有“儿童研究运动”,就不可能有杜威、蒙台梭利等人所体现的现代教育学思想的发展。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杜威、蒙台梭利幸运地赶上了“儿童研究运动”。或许,中国亦需要一场中国版的儿童研究运动,如同19世纪晚期兴起于美欧的儿童研究运动那样。
六、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属小学1—3年级的幼儿园化现象
副校长神户佳子女士介绍说,小学一年级是从生活中寻找学习点。我们在小学三年级课堂观摩了一位女教师的数学课“三角形”教学。这一教学没有知识传授,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学生们私下说话,私下讨论,完全算不上秩序井然。随行的中国课程专家十分困惑:这堂数学课为什么不能“直接”地“教学”?为什么教师不直接将三角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堂课的教学效果是不是很低?
附小有位男教师告诉我们,教师在这堂课不是教儿童,而是协助儿童;他们也有中国式“教学”,但教师的协助是贯穿一切课程的。他强调教师的教学传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协助儿童学习。他说,这种做法在日本也有争议,但那些有很好教育背景的,如从事律师、医生等职业的家长通常支持这种观念与做法,而普通家长往往担心这种教育的质量和效率。不过,这位教师强调,日本政府支持他们的这种观念和教学改革,并让附小先行,计划向全国推广普及。由此可见,日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改革已走多远。
顺便说一句,附小有日本皇室子弟接受教育,可见日本官方乃至皇室是认可这种教改方向的,甚至可以说对这种改革方向的正确性是充满信心的,否则他们是不会让皇室子弟率先接受这种教改实验的。
长期以来,我个人一直主张儿童中心、儿童本位,主张成长是第一性的、学习是第二性的,主张儿童教育应当从学习取向转向成长取向[10]。我看着这些场景,听着他们的介绍,有一种强烈的共鸣,不只是共鸣,应当说是共振——我感觉到血脉偾张,手在微微颤栗。
我们面临严重的幼儿园小学化倾向,而日本的御茶水女子大学附小已经幼儿园化。他们坚定的儿童中心的立场与观念,他们坚定的儿童中心的课程观与教学论,其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附小的课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东西,那就是“儿童哲学”。从三年级开始都有“儿童哲学”课(一、二年级是哲学基础培养), 每周1.5小时。这门课的目的是配合“公民教育”,也就是基于公民教育而开展儿童哲学课。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尊重他人意见,宽容接纳不同的人;鼓励儿童与周边他人多做交流,以便形成共同理解;共同理解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理解也十分重要;帮助儿童意识到没有当然之物,鼓励儿童对各种事物产生疑问。副校长神户佳子女士告诉我们,日本社会有尚同的传统,但为了顺应现代社会需要,日本愿意打破这种传统,以儿童哲学课来鼓励儿童成长为有独立见解的人。附小还设有“创造活动”课程,学生可以将自己的设想与教师商量,然后就尝试落实——有点像儿童哲学课,又有点像意大利瑞吉欧幼儿园的方案教学。日本小学1—3年级的幼儿园化现象是日本教育改革十分值得注意的动向之一。
参考文献
[1]刘晓东,苏令。别在儿童教育的道路上南辕北辙[N].中国教育报,2010-05-07(04)。
[2]成尚荣。儿童立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 杜威。明日之学校[M]//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21.
[4] 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7, 23.
[5]刘晓东。童心哲学史论——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82-93.
[6]王侃。哗变的学术[J].文艺争鸣,2012(10):109-115.
[7]刘晓东。中国学前教育: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M]//解放儿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64, 164.
[8]杨适。哲学的童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0.
[9]刘晓东。论教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4):18-23.
[10]刘晓东。从学习取向到成长取向:中国学前教育变革的方向[J].学前教育研究,2006(4):16-20.